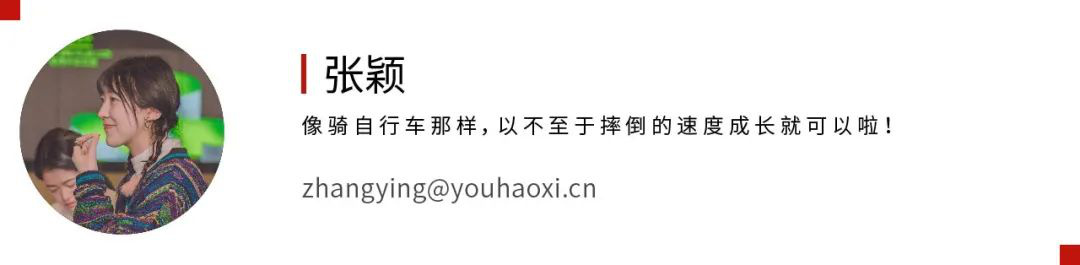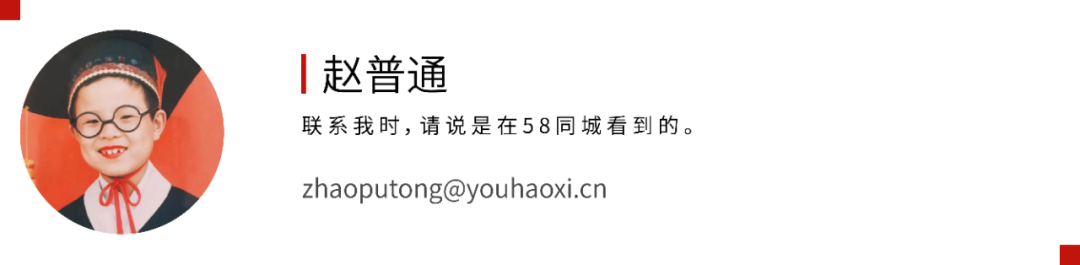|
几天前,青年摄影师朱怡遥第一次冲进喷泉里拍摄。 为保护好镜头,她穿上了雨衣,在喷泉里站着、跪着、跑着。比起捕捉到想要的画面,这些对一个摄影来说不算什么。 朱怡遥之前的镜头大多细腻、精致,这次拍《太阳雨事件》,她想用有粗糙感的镜头语言。“开拍前也想过要让画面很有风格,让人觉得这个摄影很有想法,但后来发现如果这些不能为故事和人物服务,就都要大胆舍弃掉。”朱怡遥对毒眸(ID:DomoreDumou)说。
《太阳雨事件》是今年FIRST训练营完成的7部短片之一,另外有《来客》《如斯》《属于我们的黑夜》《狗儿子》《拼图》《铁三分》共同在“对立面”的主题下创作、拍摄,组成了《对立面》这部影片。 “胆子要大”是今年FIRST训练营的口号,它意味着对年轻一代拍电影这件事的期待:拍烂了也无妨,过程最重要,拍着拍着就会有成长。 “第一,这不是竞赛,第二,我们也不是在选秀。”训练营年度导师郑大圣导演对毒眸表示,训练营的意义在于“拍”,“实打实地经历一次拍电影”。
7月19日,训练营正式开机,每组只有三天的拍摄时间和不到一周的后期时间,拍摄资金、器材和剧组各部门人员配置都是“朴素”的——但他们获得的,是一次拍片的机会,也是一次在拍电影的过程里自我审视的机会。 “拍电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是所有电影人永远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FIRST训练营走到第十个年头,在过去导演和摄影的基础上,今年增设了制片、美术、录音三个岗位。拍电影是集体作战,每一个部门都很重要。 “各部门都有很大的创作空间,不是谁的中心制,要找对人,大家一起干,所有岗位都值得尊重、应该被看到。”训练营总制片人踢替对毒眸说。 5个岗位,7个剧组,34名训练营学员聚到西宁组队拍摄。但为什么来到这里,每个人的答案并不相同。
入选训练营之前,《如斯》的导演乞少一做过一些商业项目,要满足和平衡各方的标准,写东西的时候时常觉得迷茫,“刚毕业时的劲头都没了。” 报名之前,他没什么目的性,“想来学习一下,找回最初创作和拍摄的感觉。”在他看来,FIRST是杂质比较少的地方,那些有趣的想法和自己赋予故事中人物的情感,在这里不会被限制和磨灭。 赵臻玉是《狗儿子》组的美术,她以前工作过的剧组里大多是经验丰富的前辈,这次来训练营是想看看和同龄人一起拍片是什么样的。“非常珍惜每一次和其他组美术一起聊天的机会,大家背景不同,对美术工作的理解也不同,交流碰撞会产生很多新的想法。”赵臻玉说。
王钰媛曾经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过FIRST影展,今年的她是《如斯》组的制片人。她很喜欢训练营这种在紧张的时间内创作的模式,跟公司请了长假扎在组里,和团队的“战友们”一起体验了单日长达20小时的拍摄,精力、体力和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历练,她觉得自己“可能以后再拍什么都不会怕了”。 导演艾麦提·麦麦提的短片《手风琴》入围了今年FIRST影展主竞赛短片单元,但他这次来西宁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在训练营拍出他的《来客》。一开始艾麦提并不知道会有庞大的导师顾问团来做指导,只是把训练营当做一个可以拍片子、做作品的锻炼机会。 除了年度导师郑大圣外,今年的FIRST训练营还有包括曾剑、廖拟、程马、林木、兰志强、刘浩良、许伊萌、张寒寺、温波、刘晓莎、张琪、李永一、赵又廷、周一围等电影人组成的表演、剧本、摄影、美术、声音、剪辑顾问团。
能得到这些一线电影人的指导与帮助,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宝贵的机会,但在这个过程里,青年电影人并不一定总是顺服的那一方。像FIRST影展CEO李子为说的那样,不追求结果,求的是观念的碰撞,是切磋、摸索的过程。 发现一些“本质问题” “文本太差。” 多位导师顾问在看完今年训练营7个剧本后产生了相似的感受。在追求类型和风格化的表达时,兼顾剧作的扎实和故事情感的丰沛程度,这对很多年轻的创作者并不是容易的事。
《如斯》的第一版剧本是相对类型化的,这种写法是乞少一之前工作中写作惯性的延续,但与编剧顾问开会时,对方更倾向于找故事的情感落点。“我发现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东西的不太考虑情感的东西了。”乞少一决定抛开之前的写作“套路”,重新拾起对人物情感的重视。 训练营暴露出来的问题,远不止在剧作上。 “这么多好演员过来,给你免费‘打工’,导演真能用好演员吗?”开拍前就有顾问提出这样的担心。
“如何与演员一起工作是很重要的,不能要求演员给你演一个浪漫或者忧郁,不能用形容词,要用动词,表演即行为~acting。”郑大圣认为,很多年轻导演过多的关心自己的镜头语言,关心光线和影像,但对表演的把握程度还远远不够。而在镜头里人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归结在、呈现在人上,也就是表演上。 在他看来,现场是要喊的,不是导演和摄影“交头接耳”地空说拍摄,说到哪里就得比划到哪里,得看得见、得直截的肉眼可见。尤其是要让演员明白是出自什么样的人物动机或规定情景,才造成了如此这般的一个调度,而不能要求演员演构图。
《属于我们的黑夜》的两位主演是知名演员童瑶和宋洋,老演员艾丽娅担任《拼图》的女主角,演员赵晓苏和话剧导演丁一滕在《如斯》里饰演一对兄弟——有经验的演员对剧本和表演往往有自己的思考,对年轻导演来说,如何与之沟通交流、拿到自己想要的表演也并不总是容易的。 在训练营的拍摄现场很容易出现的情况是:即使导演已经与演员对完剧本、走完戏,但具体到某一个动作、台词,演员仍然随时有自己的理解和把握,演员和导演在一个镜头拍摄前聊细节就能聊上一个多小时,计划中的拍摄时间被无限拉长。 这背后的原因往往指向一点,导演不够明确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这种不明确,影响的并不只是与演员的相处,剧组各个部门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
开机前临时改剧本、画分镜,美术组给的道具换来换去都不满意,一个镜头拍了好几条了才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机位……虽然变动是剧组常有的事,但人为因素导致的变动,意味着没有把所有的问题想在前面。 “灯光摄影美术等等,各部门要与导演讨论的,不是我认为这个好,你认为那个好。”美术顾问兰志强表示,大家要争论的不是个人喜好,而是能否为导演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服务。 明确、清醒、坚定,导演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影片的走向。机器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运动轨迹是大幅度的还是微小的,换34还是50的镜头,怎么掌握现场的节奏,怎么跟演员怎么交流等等,这些都是电影的“本质问题”。
郑大圣认为这些现场上最基本的问题,其实一点一滴地造就着电影的艺术性、决定了调性高级与否。即便是对于成熟的电影人来说,也是一样。实践的积累会让人自以为有经验可循了,但每次拍摄都会被“打回原形”,反复接受同样的挑战。 对年轻的电影人来说更是如此,充分地暴露问题,思考“拍电影究竟要解决哪些本质问题”这件事,是训练营的意义所在。 “对立面”与“共同体” 钱少、时间有限,训练营的拍摄在很多学员看来都“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时间和资金不充裕的问题,并不只发生在训练营,任何一个导演,在职业生涯的所有阶段,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
没钱有没钱的办法。 《狗儿子》组的制片人张蒲中天去租拍摄场地和房东讲价,硬生生地把原本480元一天的费用降到了340元。“要是有钱就不用费那么多口舌、直接租了就拍,但该省的地方还是要省,这样不该省的地方就可以不用那么省了。”有的美术组去买道具、衣物,超过50块钱的都要认真考虑一下,有没有更便宜、好用的选择。 钱之外,三天的拍摄时间让所有人的神经上紧了发条。 早上八点出工,拍到凌晨五点收工,拍摄团队疲惫、睡眠不足,夜戏扰民遭到投诉,制片人需要协调和“善后”的事太多,有人形容那是一种“想死”的状态; 《太阳雨事件》剧组在开拍前失去了美术,拍摄过程里丢失了某场戏B机位的素材,后期声音也出了问题……全组都在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意外中工作,片场里每当有人找到制片人樊智杰,他都要下意识地问一句:“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导演任性,整个剧组都要因为TA临时的想法而打乱计划。”“制片人觉得美术找来的景难度大、成本高,谁也说服不了谁。”“摄影和我对于剧本的理解不一样,他更倾向于用比较层次丰富的画面去表达。”吐槽抱怨、争执对立,是训练营剧组里常有的事。 在每个剧组在刚开始组队时,制片、摄影、美术和录音部门大多互不认识,与导演也往往是第一次合作,行业里资深导演带着合作多年的固定班底拍片的经验在这里变得不适用——了解、沟通的难度,是很多训练营学员最为头疼的。 最终能让他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只有一个:大家都想把片子拍好。
电影是集体创造力的结果,对训练营临时组成的拍摄团队来说,各部门之间如何充分沟通、理解,对所有训练营的学员来说都有挑战。“你要尊重你身边的人,调动所有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踢替对毒眸说。 有的组花了大量时间沟通也没有结果,片场经常出现混乱的状态,也有的组配合度极高,高效拍摄,一遍遍重来是为了更接近所有人理想的状态。 当导演“还想多拍几条,保几条”的时候,各部门全部就位,只有“过”的那一刻,片场才能有短暂的喘息时间——从“对立”到“团结”,是因为很多人相信,这是一次有意义的集体创作的历练。 “保姆团” 训练营的导师和顾问们经常调侃,自己是学员们的“保姆”。 声音顾问温波总是“冲在前面”,几次亲自上手举话筒收音,手把手地帮每一个剧组。“我常想自己参与的是不是太多了。”温波说。
在拍摄现场他经常提到,声音这个工作,没别的,就是注意力集中,“特别是外景,谁也不能白给你想要的声音,你要自己去创造,然后一层层筛选。” 兰志强作为美术顾问,在《狗儿子》组的现场问打印店墙上挂的那块布能不能换掉,美术赵臻玉找来另一块颜色的布,挂上去,兰志强还是不满意。 他认为美术就是细节,“心要像针眼一样细,一点凑合都不能有。因为每个人的审美都有局限,美术要是连自己那关都过不了,拍出来的东西就没法看了。” 摄影顾问廖拟在《如斯》组甚至亲手画分镜,和演员讲戏的时候也会适时地提出建议:这里不要这个对峙,停顿久了看起来像谍战片,这场戏的重点还是放在弟弟身上。
“我觉得这里要往上走一点,要让观众感觉到两个人经历了矛盾、化解了矛盾、回到常态,这事儿就翻篇了。”演员赵又廷在片场说。 作为训练营的表演顾问,他每天要跑几个不同的组,剧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和演员导演小声交流,这句台词应该是怎样的语气、对手戏要给出什么样的动作反应。 另一位表演顾问周一围,经常穿着组委会提供的训练营“专用”运动鞋出现,俨然融入了剧组里。必要的时候,他要跟演员搭戏,用力地关上门制造出声响来刺激演员在镜头前的反应。坐在监视器面前,也会盯着演员的表演,和导演交流是“过了”还是“差点意思”。
训练营导师郑大圣则更喜欢提问式的指导:男主角逃亡多久了?身上有没有包?他劫车的动机是什么?提问的过程是让导演梳理自己想法、判断合理性的过程,比起直接给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郑大圣更希望能引导着导演们真正想明白自己需要的什么。 在FIRST训练营,这些场景随处可见,同一天有三或四个剧组在同时开拍,几位顾问老师四处跑,常常是摄影指导到了一个剧组,美术指导刚刚要离开。“这是交接班呢!”大家调侃道。
当然,老师们给的意见并不一定要被全盘接受。有的组和顾问团聊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拍,导演和摄影有自己想要的镜头,其他人的意见只是参考,一切还得为了他们自己想要拍出来的电影的样貌服务。 演员也最大程度地配合着剧组的工作。《如斯》开拍前,演员赵晓苏和导演乞少一聊天,乞少一问:您是北京人吗?得到了赵晓苏肯定的答案后,乞少一没有说话。 “你要北京口音吗?”赵晓苏感知到了导演的担忧。“稍微盖一盖(口音)吧。”乞少一回道。 无偿劳动的演员们,用自己的方式成为FIRST训练营的一员。而做这件事的原因也往往很简单,演员刘帅良飞来西宁出演《拼图》的男主角,说是剧本打动了他:“大家都是喜欢创作、拍摄和表演的,不然谁会来这里?”
“去拍电影吧”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前期筹备、拍摄、后期,7月31日晚,电影《对立面》在西宁奥斯卡影城举行全球首映礼。 《拼图》是7个短片里唯一一部黑白的,故事来自于导演丁凯的父亲住院时对母亲说的一句话: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我写的是一个人如何从自己的困境里走出来的故事。” 丁凯说,这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讨巧的故事,和他之前的创作差别也比较大,但想到FRIST是一个允许大胆尝试的地方,丁凯还是决定来西宁把它拍出来。 《来客》的影像风格被很多导师顾问认为是有格调的、高级的。有一个镜头被导演艾麦提拍了40条,第一次拍了32条,他一直觉得节奏不对,意识到氛围不太对了之后,只能先拍下一个镜头,拍完之后又重拍了这一段,拍到了40条才满意。 “过瘾。”艾麦提这样形容他在训练营的这段经历。 乞少一觉得自己在不断地被击碎,再不断地重新站起来:“我们训练营真的是要拍出一个戛纳入围水准的短片吗?显然不是。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可过程中学习、得到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更重要的。” 《如斯》的录音王怀德说,他来训练营不只是研究声音技术的,要成为一个好的声音指导,需要更多整体的素质,“所以我想从电影出发,我是来做电影的。” 当《对立面》放映结束时,34位训练营学员站到大银幕前,很多人说看到自己参与的片子在大银幕放映,心情非常不一样:“在这一刻我才意识到,这段日子竟然会带来如此大的成就感。”
“电影是拍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 FIRST训练营的学员们大多来自国内外的电影院校,接受过专业系统的电影教育。但在电影人的眼里,拍电影不是在学校读书、学习就能完成的,他们需要靠“拍”让自己落地。 “不断地拍,不断试错。”郑大圣认为,学校教育不会告诉电影人某一场具体的戏机位应该在哪儿,灯光应该怎么打,道具的摆放怎么样会更有人味儿。“那些在现场上做出的最朴素最直觉的决定,会怎样直接影响着影片的风格,所有这些都来自于最具体的落地实操,但这个操作不会有老师在现场教你,只有靠自己不断地去试。”
训练营就是要把“拍电影”的基本问题暴露出来,让大家无可回避地直接面对,每一场、每一镜都在逼近拍电影的本质。 “所谓‘BACK TO FIRST’、‘不忘初心’就是,你概念中悬想的表达和拍电影的实在本质毫无掩饰地撞上,这个是我们永远要回头重新体会的。不然都是套路,靠套路永远拍不好电影。”郑大圣说。 所以非竞赛不选秀的FRIST训练营,也只想通过训练、拍摄,以及这个过程里遇到千奇百怪的曲折,来反复提醒年轻的电影创作者们:请更加真诚、勇敢地,继续拍电影。
|